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觀的區別和對話
2024/06/08 信息來源⚔️: 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文字:張祥龍| 編輯🧑🚀👩👦👦:燕元 | 責編:安寧
在有重大影響的西方哲學家中🏄🏼♀️,海德格爾是少數幾位與中國的道發生了真實交流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在各種東方思想中,“道”是唯一一個被他公開地、認真地討論過的“主導詞”。更重要的是👨🦼,他對於道的解釋與他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方式相一致,與他當時最關心的問題相配合⚈,反映出這“道”對於他的深遠含義。以下就將依據公開發表的海德格爾著作中四次直接涉及道和老莊的文字🧬,以及有關的事實來討論他是如何理解中國道的。
1.“道”的原義是“道路”
1946年夏天,海德格爾與中國學者蕭師毅合作👩❤️👩🟪,要將《老子》或《道德經》譯成德文🔬。此次合作以失敗告終,但這場經歷使他對“道”的字源義和衍申義有了直接的了解,促使這位已傾心於道家多年的思想家在公開出版的著作中討論“道”的意義。下面是這些論道文字中很重要的一處中的第一部分,出自《語言的本性》(1957 — 1958年)。
“道路”(Weg)很可能是一個語言中古老和原初的詞,它向深思著的人發話。在老子的詩化的(dichtenden🈯️,詩意的)思想之中👰🏼♀️🤯,主導的詞在原文裏是“道”(Tao)👨🦰。它的“原本的”或“真正切身的”(eigentlich)含義就是“道路”。但是,因為人們將這道路輕率和浮淺地說成是連接兩個地點的路徑,他們就倉促地認為我們講的“道路”不適合於“道”的含義🏌🏼。於是“道”(Tao)就被翻譯為“理性”、“精神”、“理智”(Raison)🤽🏻、“意義”或“邏各斯”。
海德格爾在這裏認為“道”的原義是“道路”。如上一節後半的詞義考察所顯示的,這種看法無可指摘。但是🪖,後來的絕大多數註釋者和翻譯者卻不在這個原本的含義上,而是在它的各種概念化、抽象化了的衍申義上來理解道🚄✖️。比如韓非的“萬物之理”、王弼的“無名無形”的“本(體)”⛹️🍾。近代人更是常常認道為“最普遍的原則”和“最終的實體”🧑🏽🏫。在西方那一邊,翻譯家們出於類似的理由而將“道”譯為“理性”“精神”“[概念化了的]邏各斯”等等。總之,海德格爾和中西哲學家們都知曉“道”是一個意味著“終極實在”或“萬物之所由”的主導詞🪧;但是,由於他們對終極實在的看法不同,對於“道”的理解也就很不一樣。大多數哲學家覺得“道路”這個詞的意思太淺近具體🤜🏿,無法表達道的普適性🧔🏽♀️、無限性和終極性。海德格爾則認為他們過於“輕率和浮淺地”看待了“道路”(Weg),將它僅僅視為“連接兩個地點的路徑”。這樣的道路就成為兩個現成存在者之間的一種現成的空間關系了。與這些看法相左🚣♂️,對於海德格爾,通過“道路”而理解的道比這種外在的現成關系要深刻得多🖐🏼。道的“原本的”(eigentlich)含義並不只是指這個字的詞源義,而是意味著它的“真正切己的”、揭示其本來面目的本源義。緊接著上面引的那一段,他寫道:可是此“道”(Tao)能夠是那為一切開出道路(allesbeweegende)之道域👩🏼🚀🧑🏻🔧。在它那裏,我們才第一次能夠思什麽是理性😽、精神、意義、邏各斯這些詞所真正切身地要說出的東西🤦🏼♂️。很可能,在“道路”(Weg)即“道”(Tao)這個詞中隱藏著思想著的說(Sagen)的全部秘密之所在(das GeheimnisallerGeheimnisse,玄之又玄者)👨👩👦👦,如果我們讓這名稱回返到它未被說出的狀態👇🏽📇,而且使此“讓回返”本身可能的話。今天在方法的統治中存在的令人費解的力量可能並正是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方法,不管其如何有效👨🏽🦳🟧,也只是一個隱蔽著的巨大湍流的分支而已;此湍流驅動並造成一切,並作為此湍急之道(reissendenWeg)為一切開出它們的路徑。一切都是道(Weg,道路)。這“為一切開出道路之道”就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現成道路🙌,不管它是物理的還是形式的、概念的🧜🏿♀️。它只能被理解為純構成的、引發著的“湍急之道路”🔲。更關鍵的是🤙🏻,海德格爾不認為這“道路”之義的深刻化和本源化就意味著理則化和概念精神化✊。那湍急之道仍然是道路🔰,只不過不再是現成的道路而已。“湍急的”(reis-senden)這個詞在海德格爾的語匯中也是大有深意的。它與他刻畫“技藝”含義時所用的“間隙”(Riss🧏🏿♀️💷,撕裂、草圖)這個詞同源,表示由幾微間隙引發的相互爭鬥又相互屬於的緣發構成態🦸🏽🔯,因而是“湍急的”👩🏽🎨,擺脫掉一切現成狀態而發生著的。從初期海德格爾講的現象學和解釋學意義上的“實際生活體驗”開始,這湍急和充滿了間隙引發力的道路就一直引導著他。如果他不在“老子的詩化思想”中認出了這湍急的和幾微暢然之道,這位開道型的純思想家能被中國古道吸引數十年嗎?
2.“湍急之道”就是緣構的(ereignende)“境域”
這種為一切開出路徑的道路在海德格爾看來就是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構成域。他寫道🐉:對於思想著的思想來說⏭,此道路應被視為一種境域(die Gegend)👩🏿🌾。打個比喻👬🏼,作為域化(das Gegnende)的這個域是一塊給予著自由的林中空地(Lichtung),在其中那被照亮者與那自身隱藏者一起達到此自由📠👩🏼🍼。這個自由的並同時遮蔽著的域的特點就是那個開路的驅動。在這一驅動中🏥,那屬於此域的各種路出現了🧌💒。這裏,將道路視為域並不主要表示從“線”推廣到“面”或“立體空間”,而是意味著從現成態躍遷到緣構態,從平板發散的觀念表象思維轉化到有境域可言的構成思維。湍急之道一定要通過自身的陰陽“間隙”引發出領會境域🅾️,在林莽幽深、風雨晦暝的深處開出“一塊給予著自由的林中空地或澄明境地”。而且🟧,這種湍急的、充滿“間隙”的道境不只是被照亮的揭蔽狀態🎐,它同時還保持著黑暗深沉的那一面💠。也就是說🏄🏽♂️,這境域的自由不是單向的🧝🏿🤽🏼、只知消耗的自由,而是有“回旋余地”的、含有幾微機製的自維持著的自由👋,因而是真正切身的自–由。正如第8章第二節所言,海德格爾的基本思想方式就是緣構境域式的。他的每個重要思路,不管是“實際生活的體驗”“形式指引”“緣在”“在世界之中”“牽掛”“先行決斷”“時間”“歷史性”“語言”“詩”“自身的緣構發生”等等🧜🏻♂️,無不具有一個回旋互構的趨向勢態📻,並只在這構成勢態中而非普遍化和概念化中得到揭示並獲得自身的意義。按照這些思路,終極的實在,不管稱之為“存在”“神”,還是“天道”,只能是這緣發境域本身,而非任何脫開境域的實體🙎🏿♂️。可見,海德格爾對於中國道的“開道境域”的理解就出自他最貼己的思路:“自身的緣構發生”(見第7章第三節)🥹😮。這樣🥷🏼,我們就讀到他論道的另一處文字🪇:人與存在以相互激發的方式而相互歸屬🙎🏻。這種相互歸屬令人震驚地向我們表明人如何被讓渡給(vereignetist)存在,存在也如何被人的本性所占有(zugeeignetist)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個構架中盛行的乃是一種奇特的讓渡(Vereignen)和占有(Zueignen)。讓我們只去經歷這個使得人與存在相互具有(geeignetist)的構成著的具有(dieses Eignen);也就是說🖊,去進入那被我們稱之為自身[身份]的緣構發生(Ereignis)的事件👼🔬。“自身的緣構發生”這個詞取自一個從出語言用法。“Ereignen”原本意味著:“er-aeugen”🧑🧒🧒,即“看到”(er-blicken),以便在這種看(Blick)之中召喚和占據(an-eignen)自身。出於思想本身的需要,“自身的緣構發生”現在就應該被視為一個服務於思想的主導詞而發言。作為這樣一個主導詞,它就如同希臘的主導詞“邏各斯”(logos)和中國的主導詞“道”(Tao)一樣難於翻譯。在海德格爾那裏👎🏻🙎♀️,“自身的緣構發生”這個詞所刻畫的是一種將任何問題追究到窮極處時必然出現的終極構成狀態🕑。表象的和概念的思維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二值的;它探討任何問題時,總要將其分成兩極🤼♀️,然後再尋求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先構造出這樣一個有形或無形的框架💯,它就無從下手✍🏻。認知一定要由主體相對客體講起;認知對象一定有形式與內容之分;終極存在要麽是實體,要麽是性質;這實體要麽是一,要麽是多;人的本性一定要從物質(肉體)和精神(心靈)來考慮;人的認知能力也就要分為感覺直觀和理智思想兩層;研究的方法則要從分析或綜合開始;等等🧏🏼♂️♻。然而,海德格爾從他早年的思想經歷中已體會出,用這種方法永遠達不到對終極問題的中肯解答。現象學的“到事情本身之中去”和“範疇直觀”的新思路在某種程度上咬開了這種二元化的現成硬殼,因為它要求在一起手處便有雙方的相互構成👩🚒;比如“實際生活經驗”中已有非概念化的理性和意義,用不著更高的形式規範來授予📄,而且,海德格爾發現,即使是極敏感出色的哲學家🦢,比如康德和胡塞爾,當他們自身造成的思想勢態(“先驗的想象力”“意向構成”)要求著一種終極突破,即在終極視野中消去二值框架的有效性時,也還是不能跨出這最關鍵的一步,因為他們確確實實地感到:如果消去了這最根本的大框架,就一切都不可測了。於是,在終極問題的關鍵處,他們也就只能靠在分叉之間的滑來滑去維持一種不生育的平衡。

作為一位有過千辛萬苦的思想探求歷程的思想家,海德格爾深知這種“畏(縮)”的某種合理性,離開框架而沒有真切的緣發機製就意味著對一切思想成果的放棄🥻,或新的形而上學構架的出現。他提出的這個“自身的緣構發生”就旨在做這最重要又最危險的“畫龍點睛”的工作,讓思想在終極的尖端🙇🏿,在令康德、胡塞爾😪、亞裏士多德也把持不住的打滑處維持住一個純發生的平衡。因此🧑🏼🍳,二元框架的效力被消解🌔,範疇“間隔”被轉化為引發“爭鬥”的幾微“間隙”🔧。這裏沒有二值構架的簡單拋棄,就像神秘主義者所希望的,而是它的轉化、間隙化和勢態化。思想的全部微妙處、痛切處🥖👩🏽、得大自在處盡在於此🤦🏿。說這“自身的緣構發生”就像古希臘的邏各斯和中國的道一樣“難於翻譯”,也是極有深意的🧝🏻♀️🚭。首先,它表明了在海德格爾的心目中🏃🏻,這三者的含義都超出了本質上是分叉的概念名相所能傳達者,所以無法被某個現成的詞翻譯,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被人用來翻譯“道”的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與語言無關;恰恰相反,這些詞義就在純顯現的或“讓其顯現”的語言經驗中被當場引發出來並保持在這語境裏。就在上面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海德格爾動用了德文的和他自創的一切純勢態的語言手段,去粘黏、影射🔘、牽引、開啟和維持住“Er-eignis”這個詞的純緣構的含義,而絕不讓它被現成化為任何一種現成觀念。這是語言本身🐦、思想本身在終極處吐出的氣勢磅礴的火花和劍芒,根本無法一一對應地翻譯,但可憑語境本身的意義勢態而相互領會。這也就意味著,“緣構發生”只能被理解為本身充滿意義勢態的境域。“這個自身的緣構發生是這樣一個自身擺動著的域,通過它✍🏽,人和存在在其本性中達到對方👰🏽♂️,並通過脫開形而上學加給它們的那些特性而贏得它們的緣構發生的本性🚪。”從以前對老莊之道以及其他天道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德格爾用“(自身的)緣構發生”來比擬中國道是很有見地的📵。這天道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可道”對象🗣,包括形而上學理論框架賦予的對象,卻能以各種(儒🚵♂️、道♛、兵、法、禪)方式被引發👩❤️👩、被充滿勢態地維持在了真切的終極領會處。這是一切觀念達不到的😶、讓他們或“過”或“不及”的至誠時中之處和任勢乘化之處💸。《老子》講:“反者,道之動”💂,是因為這道在根本處是不平靜的😵💫,它那裏沒有可供概念把捉者,只有在相反相成的“惚恍”和“混成”中構成的象、物、精、信。所以,老莊和其他天道思想家的言論中到處是“反”語和構境之語😧。思想的湍急之處,語言的大機必張,在回旋投射中彰顯出那“不可被說”者和“難於翻譯”者。
3.道與語言
以上的討論已表明,終極實在不是緣境之外的實體或意義單位,而就在境域中構成自身。所以🏕,表象的、概念的🦸🏽♂️、傳送式的語言手段永遠對付不了這樣的非現成終極👷🏻♂️,因為它實在是貼近惚恍得如鬼影附形😇、與語言本身難分彼此。這種實在的含義只能在語言本身的運作中純境域地顯現出來🖖、道將出來。因此🕌,很明白這層道理的海德格爾在討論了道路之道的非現成性和構成域性之後,說出了這樣一話:“很可能📡,在‘道路’(Weg)即‘道’(Tao)這個詞中隱藏著思想著的說(Sagen)的全部秘密之所在。”對比了“自身的緣構發生”📚、“希臘的邏各斯”和“中國道”之後,他這樣寫道:“將此緣構發生思索為自身的緣發生(Er-eignis)意味著對於這個自身擺動的境域的結構(Bau)進行建構(bauen)👇🏽。思想從語言得到去建構這種自身懸蕩著的結構的工具,因為語言乃是最精巧的、也最易受感染的擺動。它將一切保持在這個自身緣構發生的懸蕩著的結構之中🏄。就我們的本性是在這個懸蕩著的結構中所造成的而言🥷🏼,我們就居住在此自身緣構發生之中。”如果沒有上一節的討論,海德格爾的這種“道言觀”很可能會令一些人感到牽強。我們也知道🧄,海德格爾在與蕭師毅的合作中曾一再追問“道”在中文中的各種意思🆗。所以,他應該知道“道”這個字所具有的“言說”之義,盡管蕭師毅很可能不會向海德格爾建議這個意義與老子的“道”有何重要關系。然而,就憑上面已講過的學理本身的內在要求,海德格爾就可以達到“‘道’這個詞中隱藏著思想著的說的全部秘密之所在”的結論。它比任何考據都更重要👝。海德格爾之所以講到“老子的詩化思想”,不只是由於他知道《道德經》由韻文寫成,更因為他認為老子關於道的思想本身就是詩性的👅😮💨,或由語言本身的構成勢態“道”出的𓀜👂,而非是作為命題對象被表達出的。此外,上一節的討論也已表明🤷🏼♀️,揭示出“道”本身的“道言”維度對於復活道的原義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4.道、技藝與技術
海德格爾談“道”引述老莊的四篇文章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涉及“技術”和技術性的“方法”😮。這與他對道和老莊的理解以及他本人的學說脈絡有關。“湍急的道路”意味著道與“間隙”以及“技藝幾微”的含義緊密相關🅱️;“老子的詩化思想”、“語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等講法又點出了道與語言的詩性之思的關聯。而且,中國的主導詞“道”也與海德格爾的主導詞“自身的緣構發生”相提並論。然而🦸🏽♂️,我們知道,技藝、詩、緣構發生的含義都與他討論的技術問題的思路直接相關。海德格爾一再提醒,技術和方法有著“令人費解的力量”,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現實的一切現實性”。在他看來,通過技術構架去經歷實際存在是我們這些在西方文明影響圈中的現代人不可避免的命運,因為這技術就來自人的技藝本性和西方古希臘概念哲學的聯手🙇🏽。這種技術和方法威脅到了我們的生存境域,因為它只會以“整齊劃一”的方式“沖壓”我們的生存形態。“這種[術]方法🧎♀️,所跟隨的實際上是‘道路’的最極端的蛻變和退化的形式💇。”但是,即便是作為道路的最退化的形式,這技術方法也還是與道和緣構發生有斬不斷的關聯。所以,技術造成的歷史命運不會被“不要技術”的意向和做法所改變;改變只能來自追溯這技術的技藝和“自身緣構發生”的本源;以求在這種回復之中“脫開形而上學加給的那些特性”而返回到人的緣構生存形態之中去。正是在這個追本溯源的轉化努力中🏅🤚🏽,海德格爾最強烈地感受到了中國道的思想吸引力🧑🎤。在他看來,這道是“湍急的”🧙♀️,也就是充滿了技藝幾微(詩、語言)的引發間隙的,走上這種道路的思想就勢必脫去觀念化的現成思路和價值取向🚵🏽♀️🚌,在由這間隙引發的而不是範疇割裂的緣構發生的境域中重新贏得自己的本性。因此,在並提“自身的緣構發生”與“中國道”之後🎤,海德格爾馬上討論了這緣構發生之道對於解決技術問題的關鍵意義:“一個在這樣的緣構發生中出現的對於這個[技術]構架的轉化——它絕非單靠人的力量可以做成——帶來的是一個此技術世界的緣構發生式的回復,即從它的統治地位轉回到在一個境域中的服務。通過這樣一個境域,人更真態地進入到此緣構發生中🛣。”這種“技術世界的緣構發生式的回復”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人的緣構發生的原初方式不是現代技術而是技藝活動,特別是詩化的活動。人類的唯一希望——這個能“救我們”的神——就是隱藏在技術本質中的詩性幾微和境域。在這方面,老莊所代表的中國道的“詩化的思想”就有“無用之大用”🤾🏽♀️、“無為之大為”。“此道路即是那將我們移交給我們所屬於之處[的力量]👨🏻🦳。……是那為一切開出道路之道域⤵️。在它[“道”]那裏,我們才第一次能夠思索什麽是理性、精神、意義、邏各斯這些詞所真正切身地要說出的東西。”西方的概念“理性”形成了技術本質中的硬性的一面;對於這種理性的非概念前提(湍急的人生生存體驗)的開啟意味著“思索……這些詞所真正切身地要說出的東西”🧝🏻♂️,這也就是從根本上化解技術的“統治地位”🍽,使之轉回到服務於人生境域的柔性角色中。以這種方式,這條中國的思想道路“將我們移交給我們所屬於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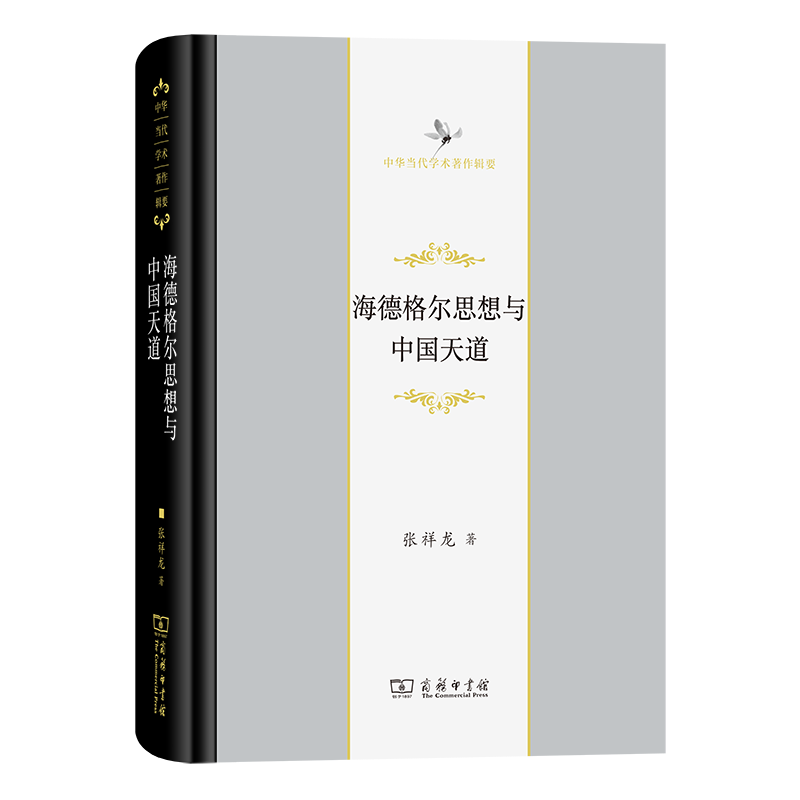
因此,海德格爾引用老莊原話的那兩處都涉及讓技術“回復”到緣發生境域這個當代最重要的問題。在《思想的基本原則》(1958年)中,他這樣寫道🧑🏽🎄:此[與黑暗相緣生的]光明不再是發散於一片赤裸裸的光亮中的光明或澄明“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困難的倒是去保持此黑暗的清澈📕;也就是說📵,去防止那不合宜的光亮的混入, 並且去找到那只與此黑暗相匹配的光明𓀐。《老子》(第二十八章, V. v. 斯特勞斯譯)講🤜🏼:“那理解光明者將自己藏在他的黑暗之中”[“知其白,守其黑”]🥿。這句話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人人都曉得、但鮮能真正理解的真理:有死之人的思想必須自身沒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對於海德格爾的後期“行話”以及本章第一節所討論的問題缺少了解的人無法理解這段話💂🏽♀️。“光明”“澄明”意味著揭蔽狀態💂🏽♀️,“黑暗”意味著遮蔽的🤶🖐、隱藏的狀態。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技術意味著一種構架化的單向開發活動,只知去揭蔽、去開發知識與有用的光明,而不知保持這揭蔽的前提,即隱藏著的境域勢態(“大地”“黑暗”)。這種技術型的揭蔽開光的極端例子和結果就是原子彈的爆炸產生的致死強光:“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的赤裸裸的光亮。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就需要尋到“那只與此黑暗相匹配的光明”,也就是與人和生命的境域勢態共尺度的光明、知識和可用性⚄。而這也正是老子講的“知其白,守其黑”中蘊涵的智慧。“白”在這裏代表陽、天、動、光亮、乾、有,“黑”則代表陰、地🖕🏼、靜、黑暗、坤、無🪨。而真正理解了光明一面的人一定會“將自己藏在他的黑暗之中”🏃🏻➡️,因為離開了這一面🆚📩,光明和剛陽就無天地之勢可依,就會幹枯為堅強的“死之徒”,或“處於陸”的魚蝦🈵。“有死之人”則意味著人的根本“有限性”或“緣在”本性。作為緣在👴🏿,人只能從自己的實際生存緣境中獲得意義和生命來源;也就是說,他必須讓自身先“沒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取得天然的緣發勢態,然後才能與這個已經與自己相緣生的世界發生知識的🟠、實用的、價值的關聯。他的真正切身的存在方式就在於不離開這黑暗泉源👱♂️、境域的勢能所在🦵🏿,以致“在白天[也]能看到星星”。生存的智慧就意味著穿透理智和實用的白晝世界而看到神意之星。這“星星”代表黑夜境域本身的“清澈”之處🩴。海德格爾在他《出自思想的體驗》的詩中寫道👩🏽⚕️:“朝向一顆星星🧜🏽,只此而已😱。/思想就意味著收斂到一個所思;/就像一顆星星,這思想保持在世界的天空。”細細體會《思想的基本原則》中的這一小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看出海德格爾前期思想過渡到後期的契機所在,即以“先行的決斷”或“去除遮蔽”為特征的真態生存方式學說為何一定要改變為以開合互構為特征的緣構發生說。此外💇♀️🫃🏿,海德格爾在《流傳的語言和技術的語言》中討論莊子《逍遙遊》末段(論“無用之大用”)的文字也包含類似的思路🤲🏽。只是在那裏,“有用”取代了“光明”的地位,“無用”取代了“黑暗”的地位👩🏻🍼👨🏻🍳;“此無用者正是通過不讓自己依從於人[的標準]而獲得了它的自身之大[即‘大樹’之‘大’]和決定性的力量🤦🏼♀️。”由此,也可以感受到中國天道的智慧有多麽深遠的🖖🏻、還隱藏著的思想維度可以開發。通過海德格爾這座宏大的、充滿了引發“間隙”的思想橋梁,那被人講疲殆了的甚至宇宙論化了的“陰陽”學說似乎一下子恢復了它原發的純思想勢態,不但可以與西方哲學中的問題產生“意義的粘黏”🤵,而且勢必被牽引到構成人類實際生存的歷史運作之中👶🏻🏊🏻♀️。本章第一已經講到,發自技藝幾微的活動與技術活動的不同就在於前者不是單向的,只知用勢和耗勢🧑🏽🎄;而是能“知其白🎩,守其黑”👨🏿,在用勢的同時玄妙地蓄勢或轉化出新的生存勢態。這也就是老子和孔子的詩化之思所要開創和回復的天下大化的人生境界🧜♀️。只要還有人生和世界,這智慧就不會過時,如果我們還能領會這“時”的純勢態的和純機緣的道境含義的話🐩。
(本文節選自《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註釋略♤。)
轉載本網文章請註明出處